美利坚爱国主义的问世
- 经济
- 2025-04-02 12:55:03
- 19
“爱国”与“叛国”的法理困境
只要没有宣布独立,各殖民地的居民就仍然是英王臣民。尽管大陆会议申明,向英王军队动武只是出于自卫,绝非叛国,但十三个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究竟是走向和解还是完全独立仍然不甚明朗。对殖民地前景缺乏共识,同时又要继续支持前线,稳定后方,这就是各地面临的窘境。显然,利用社会情绪来惩戒“公敌”,以遏制托利派的敌对行为是辉格派为数不多的选择,因为援引《叛国法》进行惩处的权柄尚且在英国当局与殖民地亲英派手中。
对于独立前夕的殖民地人而言,法律层面上的叛国罪绝不是一个陌生概念。1351年,英王爱德华三世第二十五年,议会通过了《叛逆法》,第一次以制定法的形式规定了构成叛逆罪的具体内容。《叛逆法》区分了重叛逆罪和轻叛逆罪。重叛逆罪包括:想象或设想国王、王后及其长子和嗣子之死;冒犯国王的伴侣、未婚长公主与国王长子和嗣子之妻;在境内向国王发动战争,依附于国王的敌人,为他们提供帮助;伪造国玺、王玺和国王的货币;明知是假币还将其带入境内,并在境内使用;杀害御前大臣、首席财政大臣、大法官、巡回法院法官以及所有在履行公职中的法官。另一类罪行属于轻叛逆罪,包括:奴隶杀主,妻子杀夫,以及信徒或低级教士杀害主教。显然,在法理上被界定为“叛逆”的举动,是本应效忠和服从王权、父权和神权的人直接严重冒犯了这些权威。随着国家主权逐渐从王权中分离,叛逆罪中的重叛逆罪也逐渐等同于“叛国”。本章所要讨论的“叛国”,主要是叛逆罪中属于重叛逆罪的这一部分内容。

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
亨利八世第三十五年制定的《叛逆法》宣布,所有诽谤国王的公开言论和文字都属于叛国行为。爱德华六世第一年新的《叛逆法》出台。新的《叛逆法》除了保留直接非议国王至尊地位以及直接否认王位合法性的文辞之外,不再将1534年《叛逆法》中规定的其他攻击性言辞定为叛国。到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王家律师对原有法律条文的内涵予以扩充,新的叛国罪从中构建而来。文辞重新成为可被指控叛国的罪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以文字定(叛逆)罪的做法在由国王掌控的法官手中被推向了极致。著名的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ydney)叛国案,大法官乔治·杰弗里(George Jeffreys)在只有一位目击证人的情况下,便将西德尼反驳菲尔默的未发表手稿列为关键证据,最终使得西德尼叛国罪名成立,被处以绞刑。
光荣革命之后,叛国罪的程序规则获得了专门立法。1696年议会通过的《叛国审判法》为受审方提供了一系列保障公平审判的权利。其中,始于1547年爱德华六世第一年《叛逆法》的双人证规则,被更严格和明晰地确定下来。双人证规则是指:叛国罪名的确定必须要有两名“合法目击者”,“在誓词之下指证同一公开行为”,或者是“分别指证构成同一叛国罪名的两次公开行为”。 此外,叛国案的被告还有权在开审五日之前获得一份隐去证人名单的公诉书,在开审两日前得到陪审团成员名单。被告有获得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所有对叛国罪的公诉必须在叛国行为发生后的三年之内由大陪审团决定提起控诉。

1773年纽波特的葛斯比号事件
帝国危机爆发之后,英国政府曾三度考虑以司法手段严惩殖民地反抗活动的领导人,分别是1768年殖民地人对“汤森税法”的抵制,1773年纽波特的葛斯比号事件(Gaspee Affair)以及1774年波士顿的倾茶事件。可是,如果在殖民地开庭审理这类案件,由当地人组成的陪审团极有可能做出无罪裁定,因此将嫌疑人带往英格兰开庭成为关键。英国政府的考虑依据的是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叛国法》。前者规定,在海外发生的叛国行径,将送交王座法庭审理;后者则规定,所有否认普通法效力、拒不执行制定法的行为,均为叛国。英国政府的动议引起了殖民地人的警觉。激进派高呼英国人的自由权利,痛斥异地审判乃是英国内阁的新一轮阴谋。“葛斯比号”被焚事件后,英国政府悬赏重金搜罗人证物证,然而殖民地人拒不配合,导致取证困难,最终迫使当局放弃了司法手段,转向立法制裁。同时,将犯事者“拖去三千英里之外”的异地受审,反被殖民地人列为英国政府“失义”的又一项暴政罪状。
英国当局几度试图以叛国罪为名惩治殖民地反英运动的领头人物,从而分化少数激进人士与殖民地广大居民,压制殖民地的独立势头。接替托马斯·哈钦森的马萨诸塞新总督托马斯·盖奇到任之后就两次以总督名义发布公告,先后谴责波士顿通讯委员会和殖民地大会是在图谋“叛国”。新官上任的盖奇到达马萨诸塞之后,发现总督权威在当地已荡然无存。马萨诸塞激进的民情经由盖奇汇报给了达特茅斯伯爵。达特茅斯伯爵再向皇家法律顾问总检察长爱德华·瑟洛(Edward Thurlow)和副总检察长亚历山大·韦德伯恩(Alexander Wedderburn)征询殖民地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叛国。这些报告和文件成为英国议员与政府高层判断马萨诸塞人以及殖民地人正在谋反叛乱的主要证据,也为乔治三世先后宣布马萨诸塞局部作乱与美利坚人公开叛国的皇家宣言提供了依据。
殖民地的亲英派作者在小册子与报纸专栏中传递并呼应了皇家官员与英国官方的态度。他们在公共媒介上“宣判”激进派的“叛国”行径,意在告诫与警示。丹尼尔·莱奥纳德就在他的“马萨诸塞人”系列中专辟一篇大谈叛国罪。莱奥纳德刻意完整地引述了叛国者被游街示众、公开处决和裂尸焚烧的酷刑过程:“罪犯,既不能乘囚车也不能步行,而是被拖去绞刑架;他的脖子被吊起,然后直接被斩首;在他还有呼吸时取出他的腑脏,将之焚烧;他被斩首,他的身体被大卸四块,其首级和四块躯体交由国王处置。”除酷刑之外,罪犯也将被褫夺一切财产,包括妻子的嫁妆,同时导致血统败坏(corruption of blood)。
殖民地人的一系列反英举动,在英国政府高层与殖民地保守派看来,早已等同于“向国王发动战争”,是叛国无疑。莱奥纳德专门列举了“向国王发动战争”的内涵:“武装反抗制定法”,“摧毁任何贸易”,或者“任何成群结队,意图解决公共冤屈(redress any public grievance)”,都属于构成叛国的公开行为;“向国王发动战争,不是只有废除国王才算,假借改革宗教或法律,或者要求罢免昏庸的顾问,以及其他无论真伪的伸冤”都属于开战,因为这是“据国王之权威来反对国王”;“占领国王的城堡或要塞,抵御国王的部队”也是向国王开战;“所有为了实行公共革新的武装起义”,虽然没有针对国王本人,但因为目标是王权的政治权威,也都属于开战,视同叛国。莱奥纳德从判例法中挑出这些叛国内容显然指向明确。他还特别强调,叛国罪中没有从犯一说,一旦参与谋划,只要战争最终发动,那么所有的共谋者(无论是否亲自参与战争)都犯了叛国罪。莱奥纳德的思路与英国当局的策略一致,都是借叛逆罪之名,告诫广大的殖民地人警惕某些煽风点火的少数激进人士,避免与之为伍,免得毫不知情就犯下了重叛逆罪。
莱奥纳德用叛国罪警告、威胁与恫吓殖民地人立即停止反抗行为,而约翰·亚当斯针锋相对地指出,主权问题才是界定叛国罪的关键。叛国是针对主权的攻击。如果承认英国议会对殖民地的最高主权,那抵制英国议会的立法才能构成叛国,但在殖民地人的心中,英国议会对他们并无权威。相反,“如果英国议会并无合法权威”,那么“接受了委任,并将这些立法付诸实施”之人,才是“犯了公开的叛国罪”。约翰·亚当斯显然也不愿在政论中触及尚不明朗的独立问题,所以仍然将殖民地的主权权威寄托于英王之上,这才能够在法理上指责迫使殖民地人服从未经同意的议会立法行径都是针对王权的叛国。
莱奥纳德将是否承认英国议会的统治权力作为“鉴别对国家是敌是友,是爱国还是叛乱,是效忠还是造反的真正考验”。一位自称“来自汉普夏县”的匿名作者反驳道:如果按照这种标准,那么“‘马萨诸塞人’(原文斜体,莱奥纳德的笔名)就是叛国的别名;政府之友,秩序和法律的推崇者,从它们在当代已被滥用的意义来说,就成了失义、压迫、暴政和反叛的同义词”。这位匿名作者所说的不仅仅是义愤之言。他与约翰·亚当斯一样,都看到了主权所在才是鉴别叛国和爱国的关键。他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阐明了这种观点:“叛国和造反存在于对合法权威的反抗中”,而大不列颠的立法主权“无权为我们制定法律,也无权强迫我们服从”,反抗这样的法律“既不是叛国也不是造反……而是义不容辞的义务”。
正当各殖民地之间谋求联合的政治情绪最为高涨之时,盖奇发布了第一份“叛国”公告,直指波士顿激进派呼吁广泛联合、号召共商贸易禁运是在诱使民众叛国。盖奇的公告非但没有起到“当头棒喝”的效果,反而进一步触怒了殖民地的辉格派。南卡罗来纳的一位匿名作者就将叛国公告嵌入了一连串的事件中加以诠释:一方面是英国派来了“常备军”以保障法律的实施,而马萨诸塞的总督任命由“战士”取代了“律师”;另一方面,殖民地人“平和”的联合贸易禁令却被一纸“土耳其式的敕令”宣布为叛国,这恰恰说明“压迫”与“暴政”进入了新阶段,暗示“备受压迫”的殖民地人可能不得不采用更激烈的手段捍卫自由权利。除了阴谋论式的反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原始契约也是辉格派惯用的观点。这种观点坚持原始契约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暗示如果国王没有保护臣民的自由权利,就随时存在“解约”的可能性。某位匿名作者就强调,如果国王违反了原始契约,他也免除了臣民对他的效忠,同时使得政治体得以“退出帝国”,进入“自然状态”;“如果他不再是他们的国王,那他的总督……也就不再有任何合法权威来统治殖民地人”。
辉格派以殖民地人的自由权利为基点构建的本地主权观,消解了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合法性,从而论证了所有反对英国议会立法的行为并非叛国,而是真正的爱国。不仅如此,随着殖民地人开始以“共同事业”为口号,谋求捍卫自由,并在各殖民地之间达成联合,在手段与立场上形成一致,叛国也开始从捍卫英国主权的概念转变成维护美利坚事业的概念,从被殖民地人驳斥的罪名成为被主动使用的政治话语。在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之后,对“共同事业”的想象成为有纲领、可实施的具体举措。无论是攻击美利坚的自由事业、大陆会议还是联合协议,都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大陆会议结束后,费城就有激进人士高呼“但凡偏离大陆会议决议,都是叛国”,这不仅背叛了殖民地当前以及未来的居民,还背叛了“人类仅存的自由与幸福”。
与匿名作者报纸和小册子文章中的政治攻讦不一样,总督公告是具有政治权威的官方文件。虽然身为总督的盖奇已经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威信可言,但只要殖民地人还自认英王臣民,对皇家总督的叛国公告书就必须从法理上予以回应。弗吉尼亚大会上通过了一封致本地大陆会议代表的指导意见书,就直接挑战了盖奇以公告形式宣布叛国的合法性。这封被广泛转载的意见书援引了1351年《叛国法》,并且特别指出,1351年《叛国法》以明文确定了构成叛国罪的各种行为,就是为了防止“暴君”滥用专权,随意捏造叛国罪名。其言下之意显然是谴责盖奇的公告假借王权之威,随意捏造叛国罪。
要从法理角度反驳殖民地人的抗争行为构成叛国,就必然不能承认英国《叛国法》长期积累形成的规则,尤其是亨利八世第三十五年修改的《叛国法》。这项法律是英国当局能够通过异地审判裁定殖民地人犯了叛国罪的主要法律依据,也是弗吉尼亚大会给出的指导意见中绝口不提爱德华三世之后《叛国法》如何发展的原因。殖民地不少地区更是将反对亨利八世第三十五年的《叛国法》和抗议英国剥夺殖民地人的陪审团权利放在一起,共同列为殖民地人的冤屈与苦情,提请陈诉。虽然殖民地人在政治和道德层面都可以反驳叛国指控,但要实现法理上的反转,还需要等到彻底抛弃对英王效忠才能达成。
反对英国议会是爱国而非叛国,殖民地人的逻辑自洽得益于辉格派们拆解了王在议会的英国主权观,使得对英国议会的反抗与抵制可以与名义上效忠英王共存。在大多数殖民地人的认知中,美利坚人的“爱国”并不与对英王的效忠直接冲突,反而一直都能自洽。
殖民地人采用的“爱国”话语是以自由权利为核心的一套高度理想化的政治话语。这套政治理想认为在自由的统治之下,弥漫于全社会且无所不在的公共美德是支撑统治的主要因素。英国的政坛反对派与激进边缘人物利用这套话语攻击当权的政治人物,制造了英国美德被腐蚀,自由危在旦夕的危机语境。当殖民地人套用这一政治话语,构建出暴政与自由的二元对立时,他们往往将跨大西洋的自由事业视为整体,将美利坚人的抗争视同帝国的爱国事业,他们正与母国的爱国者们携手挽救不断滑向腐朽的帝国。美利坚的爱国者们一直坚信,英国议会中有众多爱国议员同情殖民地的遭遇,支持殖民地的事业。而且,维持与英国的商贸关系,继续享有英国的保护,也符合殖民地的利益。因而,无论是在殖民地还是英国,都有一大批呼吁和解的政治势力存在。

1774年波士顿的倾茶事件
对于殖民地人来说, “爱国”话语和效忠英王之间最终的冲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战争带来的影响。随着战争的爆发与持续,前线的伤亡,后方的敌我分立,包容英美共同自由事业的“爱国”话语再难以完全支撑起战争的目的与意义。另一方面是英王的举动。邦克山战役的消息传回英国之后,乔治三世在1775年8月23日发布了《镇压叛乱与骚乱宣言》,宣布美利坚人已经处于公开叛乱状态。在不少美利坚人眼中,宣布美利坚为叛乱是英王主动切断了殖民地与帝国的联系,同时也意味着君主单方面停止了对臣民的保护,与之相对的,臣民也就可以终止对国王的效忠。 1775年10月底,乔治三世宣布美利坚叛乱的消息传回了殖民地。德雷顿如此诠释这份宣言与独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与母国的争端早已“迫使美利坚”处在了“独立状态”,但殖民地人还是寄希望于国王“会治愈我们的伤口,阻止分裂”,直到国王宣布“美利坚人不再受王权保护”,这才“终于将美利坚从大不列颠中解放了出来”。在德雷顿看来,保护的停止意味着国王“实际上解除了国王与人民之间的原始契约”,从此之后,任何一个美利坚人都不再能被诉以重叛逆罪,因为“在法律中,如果不再受这位国王的保护,也就无需对其效忠”,没有了效忠关系,叛国也就无从谈起。
除了乔治三世宣布美利坚公开叛乱,1775年11月20日,诺斯向英国议会提出了一项《禁止法案》(Prohibitory Act),要求严惩所有反叛的美利坚殖民地。《禁止法案》规定,英国海军将封锁殖民地的海外贸易,所有俘获的美利坚船只与货物都被视为战利品,无论货主的政治倾向。1775年12月20日,《禁止法案》在英国议会通过。随着乔治三世的镇压叛乱宣言与《禁止法案》的消息先后传回殖民地,1776年1月23日,马萨诸塞大议会在诸殖民地中率先发布宣言,正式宣告不再效忠英王。1776年3月23日,大陆会议针对《禁止法案》通过决议,宣布凡在公海与近岸水域上截获的英国人船只,一律视为合法战利品。内忧外患之下,殖民地宣告独立已是迫在眉睫之举,“叛国”与“爱国”之间的反转也呼之欲出。
“叛国”和“爱国”的反转
从宣示独立的文件来看,在1775年5月20日,北卡罗来纳的梅克伦堡县(Mecklenburgh County)就率先成为北美殖民地中最早宣布独立的地区。波林·梅尔(Pauline Maier)的研究揭示了1776年4月到6月之间各地通过指导意见、决议书等方式,先于大陆会议宣告了本地的独立。从政策的取向上看,激进地区率先采取了更体现独立主权性质的措施,再由大陆会议统筹与协调,以指导意见和命令的形式向各地普及推广。其实,独立态度最为坚决的是来自大陆军的意见。大陆会议代表、各殖民地法外大会与各层级的地方委员会都可以在模糊立场中左右权衡,但对于冲杀在最前线与英军作战的大陆军将领和士兵来说,早已没有其他选择。无论大陆会议如何以自卫来辩解,成立大陆军并且派遣军队与国王士兵作战,已经毫无疑问构成了重叛逆罪。这一点盖奇在邦克山战役前夕的公告中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
只有赢得一场以独立为目标的战争,才是大陆军将士们免受英国《叛逆法》惩罚的唯一可能。前线形势的瞬息万变要求军中举措必须比犹豫不决的大陆会议要更坚定和激进。军情的需要成为引导大陆会议迈向独立的重要因素。大陆军中的一桩“叛国案”暴露了不独立产生的合法性缺失与持续战争之间的矛盾。

本杰明·丘奇(Benjamin Church)
1775年9月底,大陆军的首席军医本杰明·丘奇(Benjamin Church)向敌人输送军事情报的消息被曝光,一时舆论哗然。丘奇一直属于核心的辉格派精英圈,在此之前一直被视为马萨诸塞最为坚定的激进人士。他从1775年5月就开始为盖奇将军输送情报,但从未引人怀疑。丘奇此前营造的激进派形象有多成功,其真实身份曝光之后就有多遭人仇视。然而,丘奇的“叛国”却无法被定罪。首先,殖民地现有的《叛国法》都是以英王作为最高主权象征来规定的,殖民地人即便已经掌握了实际的统治权力,却并没有名义上的政权合法性。其次,无论是马萨诸塞大会,还是大陆会议,为了避免触发实质性的独立,都在回避合法性的问题。丘奇的处置被来回推诿。丘奇先后接受了军事法庭以及马萨诸塞大会的审判与讯问。前者依据的是大陆军成立之时大陆会议通过的战争条例,但条例规定的惩罚(没有死刑)对于丘奇的“叛国”行径来说显得过轻。马萨诸塞大会的讯问则是因为丘奇在大会中拥有席位,讯问的结果也只是将丘奇从大会中除名。“叛国”的丘奇无法被定罪为叛国,只能被长期拘禁。1778年《马萨诸塞放逐法》通过之后,丘奇被放逐,最后死于海难。
为了共同事业而浴血奋战的将士时刻担心因叛逆罪被惩以绞刑,而向英军输送情报的叛徒却无法被处以叛国应有的惩罚。这就是丘奇事发之后美利坚事业的窘境。华盛顿要求大陆会议修改战争条例,使军中哗变、煽动谋反以及与敌人通信等行为能够受到死刑的惩处。大陆会议批准了华盛顿的要求。1775年底,查尔斯·李(Charles Lee)将军在纽波特首度要求托利派人士发誓不为英军提供情报与物资,并要求当地委员会配合执行,拒绝宣誓者随即被当场监禁。这份誓词首次将平民援助英军的行为定义为“叛国”。誓词不仅要求宣誓者本人不得直接帮助英军,还要求宣誓人及时向当地的安全委员会举报这类“叛国”行为。随着查尔斯·李将军一路行军,要求托利派人士发誓的做法也一路普及到了纽约。查尔斯·李将军用强制性誓词排除民众中立立场的做法,在1776年1月由大陆会议通过决议成为对各地委员会的指导建议。大陆会议建议各地将“骑墙派”视为“被蒙蔽的对美利坚事业缺乏足够了解的人”,在假设这些人的错误观念只是由于“缺乏了解,而非缺乏美德与公共精神”的情况下,要求各地加强宣传。同时,如果仍有不能接受“共同事业”的人士,大陆会议建议各地立即解除其枪械,情节严重者收监关押,同时授权各地相机向大陆军求援,完成对托利派的控制。
1776年5月10日,大陆会议全体成员通过决议,建议各殖民地建立新政府,同时委派以约翰·亚当斯为首的三人小组为决议书起草一段引言。5月15日,大陆会议讨论通过了亚当斯起草的引言,宣布“应当停止一切以王权为基础的权威,政府的所有权力都以殖民地人民的权威而行使”。 1776年6月7日到10日,经过三天商议,大陆会议全体委员会终于决定“解除对不列颠王权的一切效忠,解散诸殖民地与不列颠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6月10日,大会委派了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独立宣言”,并决定在三周之后对草稿进行讨论。一旦最终决定独立,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6月下旬,大陆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界定了美利坚的效忠与叛国概念。新的美利坚效忠以契约关系为基础,以被统治者享有保护为前提,体现了双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大陆会议的决议规定,“所有生活在联合殖民地边界之内,受其法律保护的个人,都有义务效忠于这些法律,并且都是该殖民地的成员”。拥有立法主权的政治体成为民众的效忠对象。以效忠概念为基础,大陆会议进一步界定了什么是叛国:“所有效忠殖民地的个人,……如果向殖民地发动战争,或者追随英王或其他的殖民地之敌,向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都是对该殖民地犯了叛逆之罪。”大陆会议同时建议各殖民地立法机构应尽快制定合适的法律,来惩处那些公开叛国之徒。
对于不少美利坚人而言,独立最大的意义就是终于可以惩处背叛美利坚事业的叛徒。1776年7月10日,《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凯撒·罗德尼(Caesar Rodney)在给他的兄弟托马斯·罗德尼(Thomas Rodney)的信中就分享了这种喜悦。凯撒·罗德尼认为,“《宣言》奠定了基础,后续将会制定法律来确定罪名的级别与相应的惩罚”,大陆会议以及各州政府都即将开始着手处理这个重要问题。凯撒·罗德尼显然是对于本杰明·丘奇之辈的“叛而无罚”心怀怨念。他在信中说道,“现在到了严惩那些公然作乱的敌人的时候了”,“有些人的所作所为,如果还在将来发生,那只有付出生命才能赎罪”。马萨诸塞的约瑟夫·霍利(Joseph Hawley)更是质问本州在大陆会议的代表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为什么在发布《独立宣言》的同时没有宣布重叛逆罪。 霍利强调制定一部叛逆法刻不容缓,因为“缺少它,我们的事业每分每秒都充满威胁”,这是“人民的普遍想法”,“他们希望……让所有那些试图公开摧毁本州的人士,永远消失在世间”。

第二次大陆会议签署美国独立宣言,油画约绘于1783年。
大陆会议以独立为前提,界定了效忠和叛国的一般概念;各殖民地大会则将叛国概念具体划分为不同程度的犯罪行为,并予以量刑。比如宾夕法尼亚就沿袭英国《叛逆法》的旧例,将叛逆分为重叛逆罪与包庇叛国罪(misprision of treason),区分了直接加入、援助敌军与包庇他人叛国的行为,前者将被处以极刑,后者则处以一年以内的监禁,两种叛国罪行所判处的收没财产也有轻重区别。宾夕法尼亚在制宪大会过程中制定了《叛国条例》。大部分地区在转换最高主权的同时也都相应地界定了叛国罪。虽然各州在变更主权、宣告独立、制定宪法(罗德岛没有制定新宪法)以及界定叛国等奠基举动上各有不同的顺序,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叛国的清晰界定是定义主权国家的根本问题,这是各州的共识。
通过宣告独立与各州的立宪,殖民地人自帝国危机爆发以来,尤其是“不可容忍法令”之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终于有了名正言顺的合法性。随着殖民地人对英王效忠关系终止,新的效忠关系建立,旧有的效忠与叛国也相应地转变了对象。
(本文选摘自《爱国观念的转化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兴起》,何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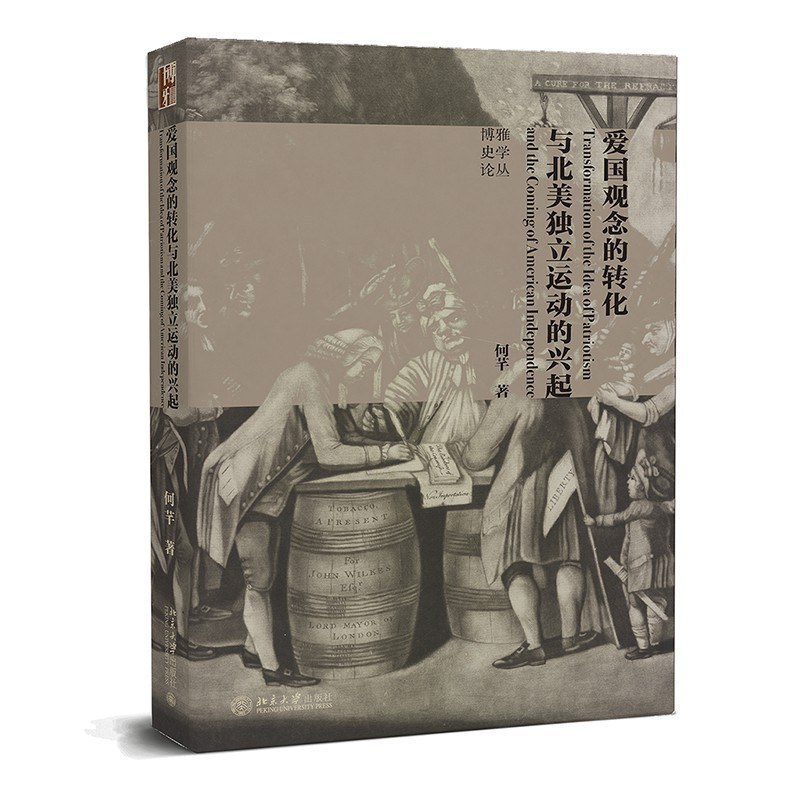
下一篇:卓沅电焊小子,青春焊接梦想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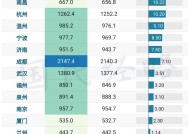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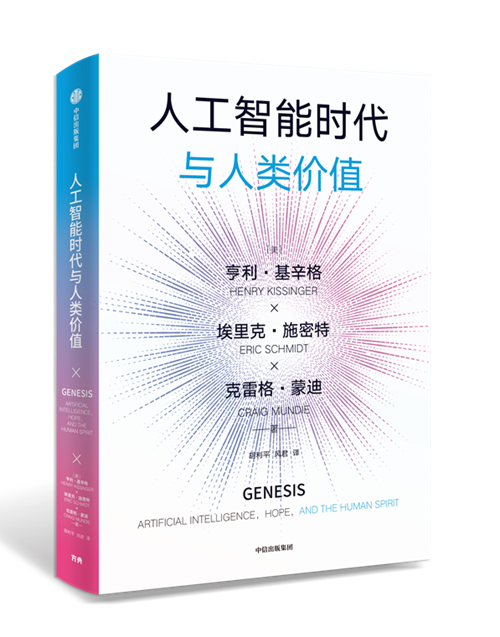








有话要说...